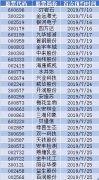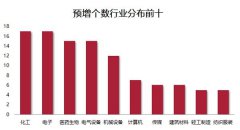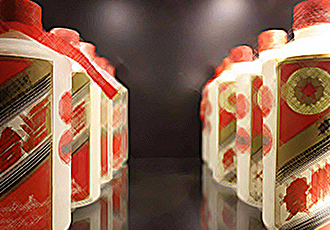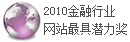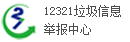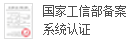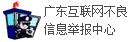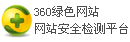信托期待一场文化复兴
2019年6月底的某一天,雪松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劲摘下了“雷震子”中江信托的招牌,崭新的雪松信托呈现在世人面前。
数月前,张主席诚意满满地出现在投资者恳谈会上。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的报道,“他特意邀请一位腿脚不方便的老太太坐到第一排,并叮嘱要照顾好她。’”。
2018年以来,金融去杠杆力度之大,“壮士断腕”四个大字常常见诸报端。疾风骤雨之下,企业资金链紧绷,此前借由信托通道进行融资的产品,逾期爆雷不断。
个中损失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每家每户皆是灾难。时至今日,大部分雷暴依然无法排解,事件进展寥寥。
从媒体公布的情况来看,中江信托近两年来踩雷产品所涉及金额超过50亿元。随后,被称为“广东第一民企”的雪松控股进场接盘,中江信托这匹曾经的业内“黑马”才看到了破局的光明。
虽然后来雪松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业界备受争议,但中江的投资人总算是吃到了一颗定心丸,尽管这颗药丸的药效尚不明确。
雪松与中江的故事远没有结束,它们是信托从业者们尝下的一颗苦果,更是一场信托文化的哀歌。
教科书告诉我们,信托制度源于中世纪英国的用益制度(“Use”,又称“尤斯”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突破封建法律的桎梏。
当时的封建地主和农民为规避捐赠和继承土地的禁止性规定,发明了用益制度,先将土地转让给他人,并要求受让土地的人为第三人的利益管理土地,将土地生产收益全部交给第三人,由此构建出信托关系的雏形。
历经几百年,信托制度走出土地,拥抱金融,成为了比肩人类想象力的强大武器,它也从西方来到了古老的东方世界。
在教科书的灌输下,我们常常不自觉地得出一个结论:信托是来自英美法系国家的“舶来品”,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信托,中国人缺乏信托文化。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抛开复杂的法律术语,我们来谈谈什么是信托。
“信”是信任、信义,“托”是托付、委托,“信托”即是基于信任的托付,可见“信”是信托之根本,“托”是信托之行为。《左传》有云:“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
在华夏文明中,信义从来都是君子的行为准则,由信任而产生的托付行为更是比比皆是。
信托行为早在先秦时代便有了雏形。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汉帛《伊尹·九主》记载:
“汤用伊尹,既放夏桀以君天(下),伊尹为三公,天下大平。”
成汤对伊尹非常信赖,将天下托付给他。
《孟子·万章上》记载:
“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型,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
成汤死后,伊尹为其后世国君治理国家,对于不肖子孙太甲,伊尹对他实行了教育和放逐,避免了成汤的政治遗产被挥霍。
国事如此,家事更是。
我们所熟知的元代剧作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讲的就是一个基于信任而托付的故事。
春秋时晋国上卿赵盾遭屠岸贾诬陷致全家灭门,赵家将孤儿赵武托付给了门客程婴、公孙杵等人,为保全赵氏孤儿,完成赵家人的托付,程婴献出亲生儿子,公孙杵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后世的明君贤士,对于这样的信托行为也多有效法。三国时期,刘备临终前将国事家事一并交托于诸葛亮,“白帝城托孤”的故事成为了千古美谈。
信托由民事行为发展为商事行为,甚至金融行为大约发生在宋代。
隋唐期间,商品经济在自然经济的缝隙中萌发,到了宋代,商品经济取得较快发展,其发达程度从画卷《清明上河图》和笔记《东京梦华录》中可见一斑。
大文豪欧阳修在《居士集》中记道:“自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为。”
可见宋人已经意识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重要性。
巨富商人并不屑于自己做买卖,而是将产业委托给职业经理人来经营管理。当时替富商打理财产的人被称为“行钱”。宋人廉布的笔记《清尊录》记载:“凡富人以钱委人,权其子而取其半,谓之行钱。”富商与行钱之间的关系便类似于今天的信托。
宋朝时,优秀的信托经理获利颇丰,收益远超过今天的信托报酬。
南宋洪迈的《夷坚志》记载了一个叫做申师孟的信托经理:
“富室裴氏访求得知,相与欢甚,付以本钱十万缗,听其所为。居三年,获息一倍……裴子以十分之三与之。”
裴氏和申师孟并非主仆,裴氏看中了申经理的资产管理能力,并与之缔结信托关系,申经理不负所托,给裴家带来了翻倍的收益,自己也获取了30%的信托报酬。
除了民营信托,宋朝还有了官办信托机构——检校库。宋代判牍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
“所谓检校者,盖身亡男孤幼,官为检校财物,度所须,给之孤幼,责付亲戚可托者抚养,候年几个,官尽给还。”
检校库的主要职能是清点遗孤的财产,代为管理,等孤儿长大成人再把财产还给他们,这样做保护了失去亲人的未成年人的权益,避免他们的财产被霸占。
检校库是如何管理资产的呢?与今天的信托公司一样,放贷款是主要的资产运用方式。王安石的女婿吴安持主管开封府检校库时候曾上奏朝廷:
“依常平仓法贷人,令入抵当出息,以给孤幼。”
宋神宗批准了这份奏折,从此检校库获得了发放贷款的“金融牌照”。《宋会要辑稿》记载,除了孤幼的财产,当时的京师国子监、军器监也将自家部门的公款委托给检校库放贷款。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有所抑制,但信托的传统并未消失,反而发展出了“家族信托”和“慈善信托”等高级形态。小说《红楼梦》中描述的利用“族田”和“祭田”制度构建隔离财产就类似于现在家族信托的做法。
《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这样说道:
“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便是有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
趁今日富贵安排好后世基本生活的保障不正是家族信托的想法吗?秦可卿建议利用当时祖茔田产(“族田”)和祭祀财产(“祭田”)不可被强制执行的律例隔离财产,不正是家族信托的做法吗?
到了近代,信托的命运在动乱的时局下风雨飘摇,信托业从未得到在金融业立足的机会,反而见风随风、见奶是娘,不仅搞投资、办银行,还做起了投机倒把的营生,信托文化在中华土地上竟荡然无存。
当时的信托大佬程联在《世界信托考证》上感慨当时的信托人“其志不在信托,而在投机。”信托机构囤积倒卖物资的行为曾一度让公众误以为信托是买卖货物而兼营运输的事业。
直至1979年,拉过煤车、洗过厕所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等来了邓小平的召唤,一家名为“信托”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他的精心运作下成立了,但此时的信托早已远离它的本源。
一方面,人民既无财要理,也无事可托,另一方面,正如小平同志说的,“经济建设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信托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
于是,信托在总设计师的指挥棒下背负起了更重大的历史责任,作为政府对外融资的窗口,探寻引进外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渠道。
80年代后,经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政府出台了进一步搞活经济的方针政策,各地计划外资金迅速增加。
1983年,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办理信托业务的若干规定》,指出“信托主要办理委托、代理、租赁、咨询等业务,以及信贷一时不办或不便办的票据贴现和补偿贸易。”
在随后的金融座谈会上,当时的央行把信托公司比作“金融的轻骑兵”和“金融百货公司”,明确了信托的定位是以银行业补充为主的金融混业平台。
尽管负担着重要的历史责任,但此时的信托早已远离了“基于信任而托付”的本义。
如今,信托业在我国恢复经营已有四十年,我们谈及信托文化已觉陌生。自恢复经营起,信托业就走上了一条异化发展的曲折道路。
“信托公司除了信托什么都做”成为从业者对信托业前三十年发展的普遍评价。即便在“一法两规”后,信托业逐步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正轨,但信托文化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信仰的丢失让信托业时不时徘徊在迷失的边缘。
诚然,中国古代的信托思想和信托行为是萌芽状态的,法律框架下的现代信托制度对我们而言确是“舶来品”,但信托文化的精神内核与华夏文化是高度统一的。
信托行业的长远发展离不开信托文化的支撑。信托从业人员要树立良好的受托文化,正确发挥信托制度优势,才能让信托行业行稳致远。
在培养信托文化的漫漫长路上,除了吸收西方信托制度和文化的精髓,我更期待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一场信托文化的“文艺复兴”,让古人的信义精神在现代信托的世界里重绽光辉。
更多"信托期待一场文化复兴"...的相关新闻
每日财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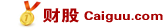

- 每日财股:中衡设计(603017
投资亮点 1、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建筑工程技术服务供应商之一,主营国内外各类民用建...[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