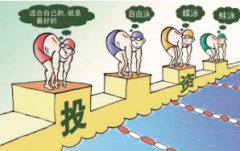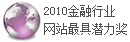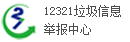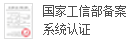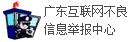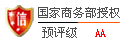麻省理工教授:中国现在本应人均收入15000美元
在北京友谊宾馆一层的咖啡厅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在谈到中国很多地方发生的拆迁纠纷时,似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他的感觉,思考片刻后,他选择用“amazing”,而在接下来我们大约一个小时的谈话里,他又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个英文单词。
Amazing,在英文中更多地用来形容令人惊叹的事情,在我看来,它很适合我们谈话时身处的这家酒店,至少在它建成时的上世纪50年代。这家号称亚洲最大的花园式酒店由中国现代最优秀的建筑家梁思成设计,并以其恢宏的规模和独特的中国味道被载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建筑史册》。“友谊”两字透露出它在当时所要招待的对象——在京的苏联专家们,今天,这家国有的酒店已对所有人开放。
然而,黄亚生在使用“amazing”这个词来形容中国时,并不仅仅是赞叹。因为当他用它来形容自己对制度的缺陷、有些国民的愚钝以及某些精英的荒谬等话题的看法时,语气所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不解和遗憾,虽然他谨慎地将“amazing”翻译成语义色彩比较中性的“不可思议”或“不可想象”。
除了像黄亚生这样的外籍人士,如今友谊宾馆的客人主要是那些来京旅游或办公的国人,三十多年来的经济权力释放,让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迅速积聚起了可观的财富,也有机会享用以往外宾才能专享的服务。落座不久,刚刚还人影稀落的咖啡厅渐渐拥挤起来。人们衣着考究,但交谈的方式让人感觉这里似乎不是一座四星级酒店的咖啡厅,而是一家普通的中式餐馆;每当隔座那位拿着手机打电话的男士的爽朗笑声响起,我都不得不把录音机放得离我的采访对象更近一些。
上一次见到黄亚生是两年前,2009年的8月,次贷危机发生整一年。当时,中国经济在政府采取的强力刺激政策下,率先出现复苏的趋势;而美国政府仍然被瘫痪的金融体系和高失业率拖得焦头烂额。2010年整整一年,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成为国际上最热门的话题,一种声音认为,历史的终结也许不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而是以国有企业、强势政府以及儒家文化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面对依然强劲的GDP数字,那些对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驱动经济的做法抱以忧虑的学者不得不尴尬面对乐观者的嘲笑。
黄亚生即是如此。明确对中国经济表达悲观态度的他也常常因此被他的西方同僚们称为“黑马”。其实在危机之前,黄亚生就对中国经济表示担忧,他认为虽然当时的GDP增速已达到11%,却是极为脆弱的,因为它受外需制约的程度相当严重。而在危机发生后,黄亚生从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中看到了更大的风险,“如果中国还是像过去那样子,只增加供给,而不去实行制度上和政策上的调整以促进消费内需,转变成消费型的经济,以后不可避免会产生生产过剩、泡沫破灭。任何政府都不能强迫老百姓消费。所以我对中国以后一年、两年的经济走势非常担忧。”
而随着通货膨胀率的急速攀升,这样的忧虑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同样的,关于“中国模式”,他的观点和两年前相比仍未改变,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实际上,早在他于2007年起笔、2008年写就的那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这一切都已经被讨论过,他的结论也早就得出: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我们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那些普世原则。
然而,在黄亚生看来,在中国一些东西过于有“特色”了,甚至会让任何一个身处现代社会的人觉得“不可想象”。他强调自己是一位温和的学者,不支持全盘西化,也不支持“休克疗法”。他希望中国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走回头路,即使慢一点。但他认为中国迫切需要一场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正在受畸形制度和特权阶层的侵蚀。
他半开玩笑地说,“可能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心理太强大了,对制度的要求很低,总觉得自己能适应,所以几千年就在同一制度的圈子里转。”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黄亚生最近都在忙一个新的调查项目,“我现在开始研究人,以前研究制度、政策,但是我觉得应该更多去注意一下人力资本的心态,甚至心理,看看一种特定的体制到底会对人的心理产生什么影响,进而如何影响他的行为。”
“中国模式”有误导性
经济观察报:最近大家都在谈“中国模式”,但对于“模式”是什么每个人说的都不同,比如你侧重于历史的方向和普世价值,另一些人则侧重于经济或政治的运行和治理方式,大家争论的焦点好像不一样。
黄亚生:我觉得还是有真正的争论的,说白了,就是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还是受国家管控的、有很强的社会主义烙印的制度更加优越,这是一种理念上的争论;从时政角度,中国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样的辩论很有意义,因为金融危机以后,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近年来的成功以及躲过金融危机是因为政府和政党制度起了强大的作用。但我很早就提出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在这三年中造成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通货膨胀、效率的损失以及大的投资项目造成的巨额负债。不仅是四万亿,加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举债,数字很惊人,如果把这些算为公债,那么中国的政府负债很可能高于美国。美国的政府负债虽然在金融危机后增加了,但私人负债减少了,所以国家整体负债并不是很高,所以我对美元非常有信心。
国外投资者对中国的态度总是很极端,因为他不了解情况,不是过于乐观,就是过于悲观。过去他们觉得美国就要崩溃了,中国马上会变成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但现在你看,“中国概念”也就维持了不到一年,现在基本上是全军覆没。成功的方面,中国符合一般的经济规律,失败的方面在其他国家也都能看到影子,所以严格来讲没有什么“中国模式”。
我最近刚去巴西,跟那里的学者讨论“巴西模式”。这个国家有段时间GDP增长达10%,也有一个强大的政府。1970年代,遇到西方的石油危机,和2008年情况很像,巴西采取了“国进民退”,从此以后一直到2003年左右,巴西经济一蹶不振。中国跟巴西相比有一些优势,教育水平、中国人的创业精神,还有一个是中国有大量的外资,所以中国可能不至于达到巴西的地步。
但是中国并不需要达到GDP2%才证明失败,只要回落到5%-6%,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从数据来看,即使是“文革”期间,中国的GDP增长也是3%-4%,现在有这么多的外资、外贸,这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30年高度增长的基础,增长却只比“文革”时快50%,并不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中国现在本应该达到人均收入15000美元,东亚国家除了朝鲜和中国,都是1万到2万美元,我们现在却只有4000美元。所以,我们的经济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贫穷经济,虽有增长但是经济水平还是很落后的。
经济观察报:你是说“经济繁荣”这个词不太适合用来形容中国这三十多年?
黄亚生: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成就,我觉得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经过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现在还有一亿农民没地、没收入、没有低保?在中国,微博上动不动就爆出有自焚的,甚至一家人集体自焚,我每看到这种消息,就像看到原子弹爆炸的新闻一样,但是好像在中国,自焚、拆迁什么的就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话题而已。
可能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心理太强大了,对制度的要求很低,总觉得自己能适应,所以几千年就在同一制度的圈子里转。我们古代有那么多的发明、创造,现在经济却搞成这样,哪里要拆迁,推土机就过去,甚至调动警察,这真是很amazing的事情。不用说在美国、欧洲这样法治完备的地方,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这都是不可想象的。
经济观察报:那么,中国未来的模式是?
黄亚生:我不是特别在乎什么西方、东方,一个中国农民有地种,财产受保护,劳动果实他能享用到,然后天天早晨起来说这是西方模式,你说会吗?根本不会,反而是精英们天天在说,这是他们西方的,那是我们东方的。但他用来在网络上写下这些观点的电脑是谁创造的,软件是谁创造的?你用的所有现代科技的东西都是西方的。西方的又怎么着了,我为什么要在乎这种东西呢?第二,如果让中国人民自己去尝试,我相信他最终选择的结果跟西方模式也不会差得很远,他肯定要搞一些契约、一套互相监督的东西出来。这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第三,如果按照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地图上的很多省份和区域都要划掉,台湾、香港不应该是中国模式的,温州不应该是中国的,广东大部分都不应该是中国的,因为它们的私营经济的发展完全都是依托西方或类似西方的模式。很多人一提西方,就像吃了苍蝇一样,这非常奇怪。有时候和人辩论,对方会说你这观点是西方观点,我听了就想,西方观点又怎么了?他在讲这话的时候,头脑中就有一个判断,因为你是西方观点,这本身就证明你是错误的,但西方观点和对错有什么关系呢,一种观点至少要通过辩论才能知道是对是错吧。
经济观察报:说你是“华盛顿共识”的拥护者是误解吗?
黄亚生:不是,方向上我是支持“华盛顿共识”的,但不是一定一步到位,要考虑中国特色,考虑中国人能接受的程度。有人常常挂在嘴上的是,西方的民主和市场发展经过了几百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承认这是漫长的过程。因为我承认这是漫长的过程所以我认为你要赶紧动手,快点做。漫长的过程不是你推迟的理由,反而是尽快开始的原因。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经济、政治改革,并不是一下子就要全部市场化,全部民主,只要往那个方向走就行,但是我的判断是,现在在走回头路,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这个时候提“中国模式”,是不是也很严重,因为它带有很大误导性?
黄亚生:肯定是,因为它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从静态上来讲是“中国模式”,一党执政、国有资产,但从动态上看都是“华盛顿模式”,大家不看变量只看常量,是非常错误的思维方式。
“转型”已经变成一种口号
经济观察报:经济发展对制度演进没有作用吗?
黄亚生:我觉得没有本质上的作用。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会改善政治体制的质量。但如果我们用腐败作为衡量体制质量的一个指标,那我相信大部分人会认为中国现在比以前更腐败了。没有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本身不会自动提高体制的质量。比如上访、冤案,二十年以前没有这么多,八十年代冤案都是文革遗留。在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当中,有一种特别普遍的看法,那就是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计是有矛盾的,贫富差距必然要加大,才会有经济发展。作为精英这样振振有词,也是我所不能想象的。没有任何统计证据来说明这个观点,我所知道的正相反,贫富差距不大的国家发展是最快的,而贫富差距非常大的国家在经济上一塌糊涂,拉美就是这样。这就像说一个家庭要挣钱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代价,就是孩子得饿肚子,多奇怪的逻辑。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家庭有人饿肚子那就说明它的经济模式失败了,不管它能挣多少钱。
经济观察报:中国政府近些年来经常谈“转型”。
黄亚生:对,现在某种程度已经变成一种口号,做什么都叫转型,都叫改革,但实际上很多是反改革的,是逆转。“改革”在中国好像已经变成一个很高尚的政治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也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我们过去投资在钢、煤、铝、水泥上,现在还是政府来做,只不过投在新能源(1972.09,0.00,0.00%)上面。大举兴建节能城市本身就是浪费,中国现在是城市过剩,大城市人口密度是全世界大城市人口密度一半都不到,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城市,增加人口的密度来节能,为什么还要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建一个新城?政府提改革、节能,都是要保持、加强自己的权力,这个不改,中国不会有真正的经济起飞,不会有普惠式的经济发展。中国现在有很多富翁,是因为人口基数比较大,绝对数字上看比较多。如果经济增长每年8%、9%、10%,回报都给了人口的1%,当然有巨大的财富效应,但这本身是错误的。对于一个亿万富翁来讲,多给他一万块钱没有任何意义,但对于挣一万块钱的人,再给他一万块钱不得了。经济增长应该是普惠的,应该有穷人的收入增加,中产阶级的崛起,有没有富翁是次要的。西方投资银行经常将中国消费奢侈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标。中国总体家庭消费只占GDP35%,而奢侈消费却成为世界第一、第二,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崩盘的预兆。
经济观察报:也有人说,改变目前以投资为主的增长方式,中国经济很可能面临停滞的风险,会像日本在九十年代那样,失去整整十年。
黄亚生:我不认为。咱们先研究一下日本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认为是因为日元升值,这没有数据支持。日元升值以后做得最好的公司都是出口的公司,而受到打击的恰恰是那些针对内需、没有竞争的企业,包括服务业、银行业。我们担心人民币升值后出口企业受影响,有一定道理,但不用过于担心,出口企业都是私有企业,自己会努力想办法消化。另外,中国和日本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中国人的创业精神。日本的社会组织和结构就像一潭死水,这在它落后的时候是一种优势,它要奋起直追,目标非常明确,国民团结一致共同去追赶这个目标。但在它已经赶上的时候,就得有一个新的目标,而新的目标、新的思维方式、创新的东西,如果人和人想的都是一样的话,是产生不出来的;肯定是那些人种不一样,思维方式又非常不一样的国家能产生创新,美国就是这种国家。中国虽然教育体制和政治体制都非常固化,但中国人的思维还是比较灵活的,你看微博上各种各样的言论都有;另外中国人性格很强韧,他要创业,去解决他自己的问题,这个日本是没有的。所以我不觉得中国会像日本那样停滞十年,但停滞一年、两年会不会?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因为现在这种严重依赖于投资的方式,GDP早晚要低下来,硬着陆,中国的经济起伏比印度大很多,从10%降到6%,绝对有可能,而且在我看来是肯定要发生的。关键是经济滑坡的时候,还能不能维持社会、政治的稳定?这是一个问号。
扶持国资是最差的选择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在过去的三年里,国资、外资、民资三种力量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黄亚生:国资肯定是在壮大,而且国资的定义,还包括那些不是百分之百国有但和政府关系很好、生意只靠政府的企业,虽然它们本身是私有,但实际上是国家资本的附属物。而且从最近的支付宝事件来看,政府还是在限制民营和外资的。我比较高兴的是过去这五年,国家对外资政策有所调整,比如说内外收入税率的统一。但像现在这样限制外资,强迫外资转移技术,是没有效率的做法。金融危机以后又加大了扶持国资的力度,某种意义上来讲还不如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的国家对外资的政策虽然挤压了民营企业,但起码扶持了外资。扶持国资是最差的选择。没有竞争,挣多少钱都是垄断利润,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国有企业如果放开的话,我想它一天也做不下去。它对国家的税收贡献也是来自于国民为获得垄断产品所付的高额代价。更严重的是,垄断企业拿走大量的资金,你想创业就没办法了,所以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实际上都是外资通过协议在控制。你要知道中国互联网的成功多亏了有外资,中国国有的金融机构有几家支持过创业型的企业?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最近几年有成长吗?
黄亚生:我们的“中国实验室”每年做16个项目,为中小企业家提供咨询,帮助它们做商业计划。通过接触,我发现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做到一定规模后,中国的企业家都越来越重视管理,越来越重视公司制度的建设。
对于民营企业,主要还是要改变它的整个生存环境。如果是一个非常健康、法制的社会,它的行为就会改变,会加强在管理和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来赢得竞争。那些所谓“野蛮”的生长方式,如果我处在同样的位置,在同样的环境下,可能也会做。
经济观察报:你对马云转移支付宝股权这件事怎么看?
黄亚生: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件事就像那个“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协议控制是一种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的非常模糊的架构,但是中国很多互联网企业家,都得靠这个东西,他们当然希望保持,但马云把这个东西捅了出来。你可以批评马云缺乏契约精神,但我觉得更应反思经济制度本身。首先如果不限制外资,我干嘛需要你协议控制;其次国家政策对外资好像想吸引又不想吸引,模棱两可,对协议控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协议控制的风险通过支付宝事件暴露出来,将影响所有想去美国上市的互联网企业,基本上把它们的路给断了,因为美国的监管机构要保护本国投资者的利益。所以无论是民企还是外资,利益都是受损的。
牌照就是一种控制,不管是第三方支付所属的金融业还是互联网媒体,这和金融安全、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关系。而政府之所以默许而不是公开地认可协议控制的存在,或许是要寻求更深层次的对企业的控制,可能是运营,也可能是言论。
经济观察报:最终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上——不想放弃做大政府。
黄亚生:根本不想放弃,这个大前提不能改。但微观的调整怎么也调不出大的怪圈。政府的治理观念还是诉诸于道德约束、孔夫子的那套,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已经破产的思维方式。两千年都没有成功,为什么你认为现在能成功?而明明有其他成功的模式,为什么不去走?
下一篇:宏观经济“软着陆点”在哪里
更多"麻省理工教授:中国现在本应人均收入15000美元"...的相关新闻
每日财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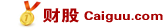

- 每日财股:老板电器(002508)
投资亮点 1.多品牌经营扩张市场空间:低端子品牌名气已运作,2010年已发展700多家终...[详细]